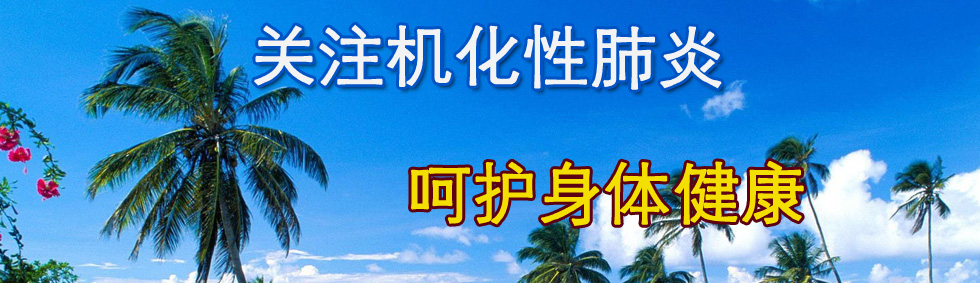
诊疗经验漫谈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1]诊断标准取消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的区别。统一分为“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两类。疑似病例判定分两种情形。一是有流行病学史中的任何一条,且符合临床表现中任意条(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具有上述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二是无明确流行病学史的,且符合临床表现中的3条(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具有上述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确诊病例需有病原学证据阳性结果(实时荧光RT-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
治疗新冠病毒(-nCoV)的三个主要方向,第一个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阻止-nCoV进入人体细胞,病毒疫苗,病毒抗体,阻断Spike蛋白和ACE结合的重组蛋白,多肽,小分子化合物都属于这一类。氯喹/羟氯喹因为可能改变ACE受体糖基化修饰,暂时也归入这一类,这涉及到免疫学效应。如果说病毒已经进入人体细胞,第二战场是阻断病毒RNA的复制,治疗靶点是新冠病毒的RNA聚合酶RdRp,老药病毒唑/利巴韦林,新药瑞德西韦(remdesivir),就是通过这个机制起作用。第三战场,就是阻断冠状病毒的蛋白酶对病毒RNA翻译出来的蛋白前体进行切割,抗HIV病毒药物蛋白酶抑制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克力芝)就是这个作用机制。
在中国,大多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患者使用了经验性的广谱抗生素,还有许多患者服用了奥司他韦,因为COVID-19的实验室诊断需要时间,而且通常很难将这种疾病与其他细菌和病毒性肺炎区分开来。[-6]
一、抗病毒治疗
此患者入院后使用了奥司他韦(医院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推荐的奥司他韦联合抗生素方案是错误的,医院在湖北的影响力对武汉以至于整个湖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都产生了不良影响。研究证明,此药对新冠肺炎病毒无效(奥司他韦抑制的是流感病毒表面协助病毒和人体细胞发生融合的神经氨酸酶,冠状病毒根本就没有神经氨酸酶,而且,新型冠状病毒侵入人体细胞的机制是冠状病毒的Spike蛋白识别人体细胞表面的ACE受体,不存在神经氨酸酶,因此使用流感病毒药物奥司他韦治疗-nCoV是无的放矢)。月4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王曼丽等研究人员,在《细胞研究》(CellReserch)发表了一篇论文,分析了7种药物在体外抗-nCoV的作用[7]。
7种药物在体外抗-nCoV的作用
注:CC50,半数细胞毒性的浓度,数值越高说明对细胞的毒性越低;EC50:半数有效浓度,数值越小说明对病毒的抑制效果越好;SI:选择性指数,为CC50与EC50的比值,数值越大说明成药的可能性越高。
结果显示瑞德西韦和氯喹在体外试验中名列前茅。相比瑞德西韦,氯喹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价廉,另一个是该药已用于临床多年,安全性高,副作用清晰。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COVID-19的试验。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对SARS-CoV-1有抗病毒活性[8,9],并且许多国家可立即投入临床使用。目前尚无任何批准用于COVID-19的治疗方法[10],而且SARS-CoV-的全球传播正在导致其他药物短缺,因此我们现在还不应该放弃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我们主张COVID-19治疗指南暂时保留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同时等待世界卫生组织SOLIDARITY试验的完成[11]。
宾夕法尼亚大学KurtM.Kunz认为:曹彬及其同事在一项单中心、开放标签的随机对照试验中得出结论,对于COVID-19患者,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与标准治疗相比未能缩短至临床改善时间,未能降低死亡率,也未能降低SARS-CoV-RNA水平。抗病毒药在感染初期用药最为有效[1],但本试验的患者在发病后13日(中位值)才被随机分组。更早启动治疗可能会更为有效,因为在SARS-CoV-感染的后期,起主要作用的是全身高炎症状态,而不是病毒致病性[13]。
本试验纳入的是重症患者,总死亡率为%,这一因素可能导致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疗效不佳,以及不良事件所致的高停药率(14%)。此外,本试验未控制并用药物:1/3的患者使用了并不建议应用的糖皮质激素[14],不建议应用的原因是它们与其他冠状病毒清除延迟相关[15]。这一情况可能导致了结果观察到对病毒载量无影响。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复方药物相对安全,并且可以很方便地调动,用于对抗COVID-19。鉴于我们对循证药物疗法的迫切需求,目前不应关上在其他人群中对早期用药开展进一步随机对照试验的大门。
密歇根州立大学DanielHavlichek,Jr认为研究是在非常时期开展,患者开始用药的时间很可能比我们目前要晚(中位值,出现症状后13天)。此外,鉴于我们对SARS-CoV-自然史的认识,本试验的主要终点(症状消退速度)可能也不是最佳终点。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组的生存分析纳入了3例从未接受该药物治疗的患者;排除这些患者后,8日生存率将有近10个百分点的绝对升幅。此外,虽然研究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本试验观察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组的住院时间和至出院时间较短。由于呼吸机数量有限且个人防护设备缺乏,因此缩短住院时间,即使只是一两天也对承受巨大压力的医疗系统有帮助。我们可能无法很快找到治疗COVID-19的特效药,我们应该从类似试验中评估的现有干预措施着手,逐步实现临床改进。
意大利巴勒莫大学医学院SalvatoreCorrao认为在对重症COVID-19患者进行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试验中,曹彬等得出结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与标准治疗相比未观察到益处。这一结论肯定会误导临床医师,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审辩式评价和逻辑分析。本试验的结果虽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在样本量小的情况下,其信号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例中,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组患者的信号包括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时间缩短5天,截至第14日时两组中有临床改善的患者百分比相差15.5个百分点,以及8日死亡率降低5.8个百分点。为了从试验的原始数据中确定适当的样本量,我们必须采用两个死亡率的比较公式。因此,本试验将需要例患者的样本量才能达到80%的统计学功效。在开展达到正确样本量的试验之前,我们不能得出强有力的结论。
曹彬团队认为:在改良意向性治疗分析中,排除随机分组后4小时内死亡且未接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的3例患者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组至临床改善的时间比对照组提前了1天。意向性治疗分析中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的潜在原因之一可能是样本量小。此外,正如几位致信者所指出的,本试验纳入重症患者,且从出现症状至用药中位间隔时间为13天。疗程和剂量可能未达到最佳。在本试验中,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组约45%的患者在第14日的病毒RNA检测结果为阳性,根据这一初步观察结果,我们推测,一些患者可能需要延长抗病毒药的用药时间,或者可能应将RNA检测结果转阴作为停药标准。
鉴于COVID-19的复杂性,我们建议临床医师在做出临床决策之前阅读本试验中关于所有结局的所有数据(包括补充附录中提供的数据,补充附录与本文全文可在NEJM.org获取)。根据不同结局和其他分析方法的结果,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仍可能是对抗COVID-19的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是该研究中评估的治疗方案之一[16]。可以认为开展样本量较大、患者病情较轻、用药时间较早、疗程较长的试验可能有助于进一步评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对COVID-19的疗效。[17]
二、抗菌药物治疗
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COVID-19患者可以合并细菌、真菌感染,及时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重锤猛击是正确的。由于怀疑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和/或继发性细菌和真菌感染,启动了经验性广谱抗菌剂和/或抗真菌方案。
二、呼吸支持技术
机械通气是COVID-19危重症患者最重要的生命支持手段,国家医疗救治专家组针对危重症患者气管插管的共性问题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气管插管问答》中指出:建立人工气道的指征是对于在%的给氧浓度及合理、规范的无创通气小时,氧合指数仍小于mmHg的患者,应尽早进行气管插管有创通气。有创通气可以更好的维持肺泡开放,防止肺泡塌陷,降低心脏负荷,降低严重低氧对全身脏器造成损伤的风险。建立人工气道后,应注意以下几点:(1)应用密闭式吸痰管进行痰液引流,避免吸痰时断开呼吸机管路,以减少气溶胶的播撒;()按需吸痰,避免频繁吸痰导致患者呛咳;对于深度镇静咳嗽反射弱的患者,注意观察呼吸机压力及潮气量情况,结合听诊进行吸痰;(3)不推荐常规进行气管镜治疗,如使用气管镜时应用三通接头避免操作中呼吸机断开;(4)使用一次性呼吸机管路,无需常规更换,呼气端放置细菌/病毒过滤器;(5)尽量避免断开呼吸机,以免PEEP消失造成肺塌陷;如因更换密闭吸痰管等原因必须断开呼吸机管路,在断开前设置待机模式,并短暂夹闭人工气道;COVID-19患者急性期呼吸驱动高,注意人机协调性,避免呼吸机频繁报警,必要时给予患者镇静甚至肌松;(6)推荐采用声门下分泌物引流(SSD)进行气囊上滞留物清除,避免断开呼吸机手法清除气囊滞留物,避免呼吸飞沫播撒;(7)避免喷射雾化器治疗,如需进行雾化治疗,首选带雾化吸入功能的呼吸机,如需外接雾化器,建议使用振动筛孔雾化器。(8)气道湿化:(中国首例COVID-19死者遗体解剖肺组织切片镜下可见弥漫性的肺泡损伤,伴有支气管上皮剥脱,纤毛脱落,鳞状上皮化生等病变;死者大部分肺泡和肺间质巨噬细胞浸润,肺泡上皮细胞增生形成双嗜性胞浆丰富的多核巨细胞,即巨细胞肺炎。大量的渗出以及白细胞的浸润,导致了肺部外观上明显膨隆、增大,重量增加。结论:肺泡损伤+粘液纤毛清除机制受损的病理学证据与流感肺炎非常相似。COVID-19患者尸体解剖肺部的表现,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不一样,没有严重纤维化,肺泡还存在,但是炎症很厉害,存在大量的粘液,非常黏,导致病人的通气不通顺。)推荐采用主动加温湿化器,特别是内含加热导丝的伺服型湿化器进行气道湿化,注意观察气道湿化效果及患者痰液情况。雾化吸入治疗上使用氨溴索雾化液、乙酰半胱氨酸雾化液(富露施);(9)胸部物理治疗:尽量避免胸部物理治疗;可采用体位引流促进痰液引流。
三、实验室检查
缺乏特异性。发病早期外周血WBC正常或减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部分患者可出现肝酶、LDH、肌酶和肌红蛋白增高;部分危重者可见肌钙蛋白增高。多数患者CRP和血沉升高,PCT正常。严重者D-二聚体升高、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性减少。
嗜酸性粒细胞减少可能提示预后不良。在一项对85例COVID-19死亡病例的描述性研究[18]中对一系列COVID-19死亡病例的特点进行总结,并对其临床特点进行描述。大多数病例是50岁以上的患有非传染性慢性病的男性。85例中81例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38例,46.91%),其次是感染性休克(16例,19.75%)、多器官衰竭(13例,16.05%)和心脏骤停(7例,8.64%)。急性冠脉综合征、恶性心律失常和DIC是罕见的死亡原因。大多数患者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早期出现呼吸短促可作为COVID-19加重的观察症状。嗜酸性粒细胞减少可能提示预后不良。联合应用抗微生物制剂对这组患者的预后没有明显的益处。
研究发现几乎所有死亡的患者外周血中嗜酸性粒细胞的绝对计数都减少了。在非严重和严重COVID-19名患者中,据其他地方报道,存活的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减少的患者数量分别为39/8人(47.6%)和34.56人(60.7%)(17人)。先前的研究已经报道,在急性感染或炎症中,循环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数量会迅速而持续地减少[19,0]。一项关于30天死亡率和嗜酸性粒细胞减少症的研究表明,嗜酸性粒细胞减少症是肺炎但没有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1]。这种效应与类固醇的使用无关。在COVID-19的病例中,这可能与SARS-CoV-引起的CD8T细胞耗竭和嗜酸性粒细胞消耗有关。IL-5由CD8T细胞产生,促进血液中嗜酸性粒细胞的增殖和激活[-4]。SARS-CoV-感染者的CD8T细胞数量较少,而且ECP和EDN这两种嗜酸性粒细胞颗粒蛋白可以中和病毒[1,5,6]。因此,COVID-19患者的嗜酸性粒细胞减少可能与SARS-CoV-病毒载量增加和SARS-CoV-引起的嗜酸性粒细胞颗粒蛋白消耗有关。尽管本研究中几乎所有患者都发现嗜酸性粒细胞减少,但许多非致命性重度和中度患者也可能发生嗜酸性粒细胞减少症。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嗜酸性粒细胞减少症在COVID-19患者中的预后价值。
在鼻咽拭子、痰、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粪便等标本中可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对于核酸检测敏感性问题,病毒分子检测通常包括几个步骤:①咽拭子取样(Throatswab),得到病毒标本。②抽提标本中的病毒RNA(其中也混杂了无数的人体自身和上呼吸道细菌的核酸)。③用一种叫做rtPCR的实验室方法,将很微量的病毒RNA特异性地扩增成DNA。④在这个反应中,加入一种荧光标记的,与病毒基因特异互补的核酸序列片断(俗称“探针”,英文名字是probe)与rtPCR的产物杂交,用莹光显示病毒RNA的存在并再次增加检测的特异性。
出现假阴性的主要原因:
①取样误差
我们都知道,普通感冒的主要表现是上呼吸道症状,如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等。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不知道什么原因,更喜欢下呼吸道的上皮细胞,临床的主要表现是肺炎。这样一来,用咽拭子取材,位置在上呼吸道,病毒就有可能躲过去了。
好的取样方式是什么呢?
是支气管肺泡灌洗,英文Bronchoalveolarlavage(BAL)。这个方法可以直接从下呼吸道取材。但需要用支气管镜,操作起来比较困难,需要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来操作,也不适合门诊。出院的病人,下呼吸道肺泡灌洗液的标本检测作为出院标准,这样才有可能更准确。
除了病毒自己的居所喜好,被感染者在取材时的状态也会造成病毒数量短暂性减少,比如,他或她刚刚漱了口或者喝了许多水。
②病毒RNA降解。
病毒RNA在失去病毒外壳保护后,对自然界无处不在的RNA水解酶是极度敏感的,几秒的时间就可以被降解,因此,在处理标本的过程中稍有不当就会出问题。这个问题在缺乏实医院可能更为常见。所以,这个检测试剂盒对使用机构的资质有严格要求。
③病毒基因在关健位点上出现新的突变
在做rtPCR时,要加入两个与病毒RNA特定位点互补的核酸片段做“引物(primers)”。如果病毒RNA与引物相杂交的片段出现新的变异,哪怕只是一个碱基,特别是三价的嘌呤碱,PCR都可能失败。这种现象不是很普遍,但不能排除。
④试剂盒质量问题
正常情况下,每个实验室对每一批试剂都要做三次的验证(validation),以确保结果可靠。检测时应该有阳性和阴性对照。在流行病暴发期间,紧张的工作中如果忽略了这个程序,也会出现假阴性的结果。
综上所述,单纯依赖病毒基因检测作为诊断和治疗效果评价标准是容易出误差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病史(是否来自疫区,有无接触史等)、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的结果结合起来,做出综合的判断。
核酸检查中尚存在有不确定的相关因素:一是部分患者短期内感染-nCOV后,可能暂未形成抗体,或者个体差异对核酸反应不敏感,可能会出现假阴性。二是核酸测试验盒是否达到%的敏感度尚有待确定。三是咽拭子的标本采取与咽部-nCoV附着量是否有关。四是实验室有不同级别的多技师进行检验操作,其中有无操作技术中的质量误差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因素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病原,科学认知仍在不断完善,病毒是否可以持续、少量的存留,导致的一种延续的状态还是一个未知数。这就影响核酸检测的阳性率。
检测-nCoVIgM抗体、IgG抗体的临床意义?[7]
IgM是首先快速产生的抗体。血液中检测到此抗体,提示近期感染,是辅助诊断指标。
IgG抗体晚于IgM抗体出现。有研究表明,随着疾病的发展,有报道称-nCoV感染者18天体内IgM抗体开始下降,IgG抗体开始上升。IgG抗体在体内存在时间较长,可作为流行病学调查检测指标。IgG阳性表明机体有感染,但不能区分是现症感染还是既往感染。换句话说,IgG阳性者可能是正在受感染者也可能是以前感染过,体内产生了抗体,是感染产生的痕迹。但是,不是所有的抗体都具有中和保护力,就新型冠状病毒抗体而言,其表达水平及其转归变化还需要更多的医学研究。
简而言之,核酸检测的是病毒RNA(核糖核酸),是病毒存在的直接证据;抗体检测是检测患者血液中被刺激产生的抗体,是间接证据。间接证据可以对临床有所提示,但仍需直接证据进行确诊。
四、影像学表现
缺乏特异性。部分COVID-19患者在发病早期,影像学呈阴性,但随诊出现肺部病灶。对于单纯肺内磨玻璃密度影(ground-glassopacity,GGO),平片漏诊率较高。CT:早期多呈单发或多发GGO,多呈肺外周、胸膜下分布优势,也可沿支气管血管束分布,或位于肺中央、肺门侧;GGO区可伴有小灶性实变区。GGO密度可均匀,也可伴线状、细网格影(铺路石征);边缘可清晰或模糊;病灶内部或周围血管影增粗(可能与肺充血、淤血和血管炎等有关)、扭曲和边缘毛糙,随着病情好转,血管影可恢复正常。随着病程进展,部分病例可逐渐吸收消散,不进展为肺实变;而部分病例病灶增多,可在原GGO区或其他部位新发肺实变,可在短期内迅速进展,重症患者可迅速发展为“白肺”样表现。病灶区可见含气支气管征,支气管壁可增厚,多为轻度增厚,但不是常见、显著的影像学表现,常被忽略;目前尚未发现单纯COVID-19影像上出现“树芽征”的病例;肺间质纤维化可导致牵拉性支气管扩张。胸腔积液、肺门和纵隔淋巴结肿大者少见。消散期,病灶范围缩小,密度减低,可完全吸收消失,也可残留纤维条索、胸膜下线影,甚至呈现“OP”样表现。部分病例呈一定的“游走性”,原有病灶消散,但又出现新病灶,临床症状反复。总之,COVID-19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点,但缺乏特异性,其受多种因素影响,呈多样性与复杂性。COVID-19的动态变化、结局与其他病毒性肺炎相似。
影像学鉴别诊断:主要与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人偏肺病毒、SARS冠状病毒等其他已知病毒性肺炎鉴别;与肺炎支原体、衣原体肺炎及细菌性、真菌性肺炎等鉴别。此外,还要与非感染性疾病,如血管炎、皮肌炎和机化性肺炎等鉴别。
六、入住ICU的患者是否得到更多的获益
大多数COVID19患者出现轻、中度症状,但严重的患者可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甚至死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诱导了与严重肺损伤相关的过度和异常无效的宿主免疫反应[4,8]。
COVID-19患者最常见的合并症是高血压和糖尿病,与以前的研究相似。
00年4月7日施焕中团队发医院、医院、医院、医院联合研究成果。研究论文[9]为来自武汉市3家医院例确诊COVID-19死亡患者回顾性分析的报告。医院例COVID-19肺炎患者进行多中心观察研究,描述了COVID-19肺炎患者的住院和重症监护过程。收集并分析了人口统计学、临床、实验室和治疗数据,最终随访日期为00年月4日。结果:例COVID-19肺炎患者的平均年龄为70.7岁,其中女性35例(3.1%)。85例(78.0%)患者有一种或多种潜在合并症。所有患者均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尤其是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甚至在疾病早期就已出现。总体而言,从出现症状到死亡的平均时间为.3天。所有名住院患者都需要入住ICU,但由于可获得性有限,只有51人(46.8%)有这样的机会。住院至死亡时间,ICU组为15.9d(SD,8.8d),非ICU组为1.5d(8.6d,P=0.)。结论:COVID-19肺炎的死亡率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尤其是合并主要合并症的老年人。住进ICU的患者比那些没有进入ICU的患者寿命更长,因为ICU组接受了更积极的治疗,包括机械通气、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和体外膜氧合。我们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此类感染的识别和临床管理,特别是ICU资源的分配。
七、新冠病毒疫苗也许是最值得期望的治疗方法
最常见的是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等五条技术路线。-nCoV疫苗研发的几个要点:第一,产能,假定目前有十万人感染,那么疫苗的需要量是千万人级别的,无法达到千万人级别的疫苗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mRNA疫苗不适合中国;第二,疫苗的成本,生产千万人级别的疫苗成本太高,对中国是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人负担不起。第三,从研发到临床实验到获批上市的时间,耗费时间太久。第四,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nCoV活体减毒疫苗的安全性就很有问题。
制备新型冠状病毒DNA疫苗的技术流程:第一是DNA疫苗的载体质粒pVax1;第二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Spike蛋白基因,病毒基因组序列张永振已经公开,拿SARS和MERS的Spike蛋白基因比对一下就可以确认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Spike蛋白基因用于疫苗制备的时候需要进行密码子的人源化和mRNA结构优化,这个步骤可以通过GenScript的软件平台完成。除此之外,克隆到pVax1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Spike蛋白基因需要对N端进行改造来提升蛋白表达水平。疫苗制备的一些细节:第一步,比较不同毒株的S蛋白序列,如果有不同,需要分布制备疫苗。第二步,将Igheavychain?-1signalpeptide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编码区融合,增加蛋白的表达水平,这对于疫苗的成功极为重要。接着对融合基因进行密码子优化和RNA结构优化,确保RNA的结构稳定,提升蛋白翻译效率。最后一步是克隆到pVax1表达载体。接下来是在93T和Vero细胞做瞬间表达,确保表达出来的蛋白大小是正确的。使用免疫荧光确认蛋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蛋白,pVax1空载体是必需的阴性对照。免疫小鼠,使用ELISpot检测疫苗的免疫性。检测注射疫苗后产生的抗S蛋白的抗体效价。冠状病毒DNA疫苗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快速,低成本,然后可以大量生产,注射也很容易。冠状病毒DNA疫苗的生产极为简单,将冠状病毒的S蛋白全长基因克隆到pGX载体里面,得到的DNA质粒溶解在无菌水里面给病人注射,生产时间一个月就足够了。RNA疫苗的时间最短,但是目前没有成功的案例。DNA病毒疫苗已经有多个成功案例,这里的成功指的是I期临床实验证明安全性和大部分接种疫苗的健康人可以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包括寨卡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
美国政府和另外一个非盈利机构资助的三个-nCoV疫苗,DNA疫苗,RNA疫苗还有蛋白疫苗,靶点都是一个,-nCoV的Spike蛋白。美国-nCoV疫苗开发的三箭齐发:中国选择了使用活体病毒毒株传统方案(使用传统方法制备活体病毒疫苗生产周期长,然后活体病毒疫苗的安全性需要反复验证)和RNA疫苗(RNA病毒疫苗根本就没有做过人体实验,所以是否有效很难说)方案。但为了保证安全性和时效性,美国选择了DNA疫苗,RNA疫苗,蛋白石疫苗这三种途径,放弃了耗时太久的传统活体病毒疫苗途径。使用传统方法制备活体病毒疫苗生产周期长,然后活体病毒疫苗的安全性需要反复验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选择这个技术途径的原因。
-nCoV疫苗开发如何取舍,以下是几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一,疫苗需要的总数和企业的产能。如果-nCoV持续流行几个月,预期疫苗最少需要一千万支。如果一个月疫情结束,疫苗就不需要了。
第二,疫苗生产的成本和技术要求。成本和技术要求太高的疫苗生产路线对中国就是不合适的。
第三,疫苗生产需要的时间,临床实验的时间还有医疗监管部门审批的时间。一个生产时间超过一年的疫苗对于这次的疫情控制也是不合适的。
蛋白疫苗的生产注意事项。-nCoV的Spike蛋白表达需要使用昆虫细胞表达系统,而且需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昆虫细胞系。首先使用Bac-to-BacBaculovirus系统在Sf9昆虫细胞生产表达-nCoVSpike蛋白的baculovirus。接着用从Sf9昆虫细胞获得的表达-nCoVSpike蛋白的昆虫病毒去感染另外一个昆虫细胞系High-Five,因为后者表达重组蛋白的效率是Sf9的10倍。
细胞病变效应分析来对抗-nCoV,这将导致产生活性良好但靶标未知的化合物。识别潜在的药物靶点对于了解药物作用的潜在机制将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肽基疫苗[30]。在传统的疫苗设计中,依赖生化试验的成本高、耗时长,需要在体外培养致病病毒,而且会引起过敏或反应反应;另一方面,肽基疫苗不需要体外培养,使其具有生物安全性,并且其选择性允许准确地激活免疫反应;[31,3]另一方面,肽基疫苗不需要体外培养,使其具有生物安全性,并且其选择性允许准确地激活免疫反应;[31,3]另一方面,肽基疫苗不需要体外培养,使其具有生物安全性,其选择性允许准确地激活免疫反应。
肽疫苗的核心机制是用化学方法合成识别的免疫优势的B细胞和T细胞表位,并诱导特异性免疫反应。靶分子的B细胞表位可以与T细胞表位相连,使其具有免疫原性。T细胞表位是短肽片段(8-0个氨基酸),而B细胞表位可以是蛋白质。[33,34]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利用免疫信息学方法设计基于多表位的多肽疫苗。
设计一种新的疫苗对于抵御全球迅速无穷无尽的疾病负担是非常关键的。[35-38]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物技术发展迅速,随着对免疫学的了解,促进了合理疫苗设计新方法的兴起。[39]随着各种生物信息学工具和数据库的进步,可以设计多肽疫苗[40,41];多肽可以作为疫苗开发中的配体。
通过比较测序,在-nCoV株中发现了广泛的突变、插入和缺失;此外,10个MHC1和MHC相关肽是有希望的疫苗设计候选者,世界人口覆盖率分别为88.5%和99.99%。基于T细胞表位的多肽疫苗是为-nCoV设计的,使用包膜蛋白作为免疫原靶;然而,所提出的基于T细胞表位的多肽疫苗需要迅速在临床上验证,以确保其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以帮助在这一流行病导致毁灭性的全球爆发之前阻止它。[4]
《柳叶刀》(TheLancet)于5月日在线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首个-nCoV疫苗(SARS-CoV-)的I期临床试验发现:该疫苗是安全的,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且能够在人体内诱导产生针对SARS-CoV-的免疫应答。这是一项在名健康成人中进行的开放性试验,第8天出现有希望的结果,最终结果将在第六个月进行评估。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验证该疫苗所诱导的免疫应答是否能有效保护人们免受SARS-CoV-的感染。试验表明,单次接种复制缺陷型人腺病毒5型(Ad5)载体新冠疫苗在14天内就能诱导产生病毒特异性抗体和T细胞应答,这使其成为具有潜力的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候选疫苗。不过,我们对这些结果应谨慎解读。研发COVID-19疫苗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诱导免疫应答的能力并不一定表明该疫苗能完全保护人类免受SARS-CoV-的感染。这些结果为新冠疫苗研发提供了积极前景,但距离该疫苗上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研发有效的疫苗是控制冠状病毒病(CVOID-19)大流行的根本解决方案。目前,全球有多个COVID-19候选疫苗正在研发当中。该试验所评估的Ad5载体COVID-19疫苗是第一个在人体上进行试验的新冠肺炎疫苗。该疫苗使用一种减毒的普通感冒病毒(腺病毒,易感染人类细胞,但不致病)将编码SARS-CoV-刺突(S)蛋白的遗传物质传递给细胞。随后这些细胞会产生S蛋白,并到达淋巴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识别S蛋白并击退冠状病毒。这项试验评估了不同剂量的Ad5载体新冠疫苗在名18-60岁没有感染SARS-CoV-的健康成人中的安全性和产生免疫应答的能力。该试验从中国武汉招募志愿者,将其分配到低剂量组(5×vp/0.5ml,36人)、中剂量组(1×vp/1.0ml,36人)或高剂量组(1.5×vp/1.5ml,36人),并进行单次肌肉注射。
研究人员在志愿者接种疫苗后定期采集其血液并进行检测,以确定该疫苗是否激活了人体的体液和细胞免疫两方面的免疫应答:1.体液免疫,即免疫系统中产生中和抗体的部分,可以对抗感染,并提供一定的免疫力;.细胞免疫,依赖T细胞来对抗病毒,而不是抗体。理想的疫苗应同时产生抗体和T细胞应答来防御SARS-CoV-。
大多数不良事件为轻度或中度,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中分别有83%(30/36)、83%(30/36)和75%(7/36)的受试者在接种疫苗后7天内至少出现一次不良反应。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注射部位轻度疼痛(54%,58/)、发热(46%,50/)、乏力(44%,47/)、头痛(39%,4/)和肌肉痛(17%,18/)。一名接种了高剂量疫苗的受试者出现重度发热,并伴随疲劳、气短和肌肉痛的症状,但这些不良反应均在48小时内自行恢复。在接种疫苗后的两周内,所有剂量组都产生了一定水平的针对SARS-CoV-S-RBD蛋白的抗体免疫应答,但不一定能够对抗该病毒(低剂量组16/36,44%;中剂量组18/36,50%;高剂量组/36,61%),一些受试者能够检测到针对SARS-CoV-的中和抗体(低剂量组10/36,8%;中剂量组11/36,31%;高剂量15/36,4%)。8天后,大多数受试者的结合抗体出现了4倍增长(低剂量组35/36,97%;中剂量组34/36,94%;高剂量组36/36,%)。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的高剂量组中分别有50%(18/36)、50%(18/36)和75%(7/36)的受试者产生针对SARS-CoV-的中和抗体。重要的是,该疫苗还在大部分受试者中诱导产生了快速的T细胞应答,高剂量组和中剂量组的这种应答更强,并在接种疫苗后第14天达到峰值。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接种疫苗后第8天,大多数受试者出现了T细胞应答阳性或可检测到针对SARS-CoV-的中和抗体(低剂量组8/36,78%;中等剂量组33/36,9%;高剂量组36/36,%)。然而,作者指出,高水平的Ad5(普通感冒病毒载体)预存免疫力会同时削弱该疫苗的抗体和T细胞应答。在这项研究中,44%-56%的受试者存在高水平的Ad5预存免疫力,这些受试者的所产生的抗体和T细胞应答相对较低。
研究发现,Ad5预存免疫力可能会减缓对SARS-CoV-的快速免疫应答,并降低应答的峰值。此外,高水平的Ad5预存免疫力也可能会对疫苗诱导的免疫应答持久性产生负面影响”。
该试验的主要局限性是样本量还不足、观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以及缺乏随机对照组,这限制了研究团队发现该疫苗更罕见的不良反应的能力,或者限制了该疫苗在产生免疫应答能力方面提供更为充足的证据。在该试验疫苗上市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Ad5载体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期临床试验已经在武汉启动,以确定在名健康成人中(中剂量组50人,低剂量组15人,安慰剂对照组15人)这些I期试验的结果是否可以重现,以及到接种疫苗后第6个月是否会出现任何不良事件。II期临床试验首次包括了60岁以上的受试者,这是该疫苗的重要目标人群。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EB/OL].00-0-18.
[]WangD,HuB,HuC,etal.Clinicalcharacteristicsofhospitalizedpatientswithnovelcoronavirus-infectedpneumoniainWuhan,China.JAMA,00Feb7,33(11):-.
[3]GuanWJ,NiZY,HuY,etal.ClinicalcharacteristicsofcoronavirusdiseaseinChina.NEnglJMed,00Apr30,38(18):-.
[4]HuangC,WangY,LiX,etal.ClinicalfeaturesofpatientsinfectedwithnovelcoronavirusinWuhan,China.Lancet,00Feb15,():-.
[5]ChenN,ZhouM,DongX,etal.Epidemiologicalandclinicalcharacteristicsof99casesof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inWuhan,China:adescriptivestudy.Lancet,00Feb15,():-.
[6]YangX,YuY,XuJ,etal.Clinicalcourseandout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hmqm.com/tslf/10753.html